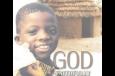一、爸爸的死
1974年2月,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。我被二姐从教室里唤出来,姐姐哭着说,爸爸死了!
爸爸死了?!“哇”一声,我失声哭起来。那一年我九岁,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。
姐弟俩哭哭啼啼赶紧往家中跑,沿途的亲戚邻居也多是到我家去的。没进家门,妈妈和大姐的哭喊已传入耳中,撕心裂肺。堂屋里的情形,深印脑海,难以忘怀:堂屋正中间,父亲躺在门板上,身上盖着红被子。母亲死去活来的哭喊,在香烟缭绕、烛光摇曳的映衬下,更是凄恻。
小孩子的我,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突然死去……我静静守候在父亲遗体旁,摸着他冰凉僵硬的手,心想爸爸可能会突然从门板上坐起来的……“死”,对于我而言,还是一个神秘难懂的事情。我看着、想着、盼着;直到拖拉机拉走父亲,运往火葬场……我才有了生离死别的感受。于是,我撵在拖拉机后面,使劲地跑着哭着……
那一年父亲五十一岁,是癌症夺走了他的生命。
随着父亲的死,童年的欢乐似乎也离我而去了。星光下,我学会了发呆:爸,你在哪里?你不回来了吗?我们姐弟几个,还是左右手不分的孩子。往后谁挣工分养活我们啊?
从那时起,“死”的恐惧和强悍,就时常钻入脑中,让我既惊惧又无奈。我时常躲进母亲怀中,说:娘,我怕,我怕,怕你也死去!母亲用瘦弱的双手搂着我,极力安慰:儿啊,别怕,娘不会死。有菩萨保佑!
菩萨保佑!我猛然一惊:就是那尊似笑非笑,爸爸妈妈小心翼翼拜了一辈子的菩萨吗?爸爸死前每天向它三叩九拜,还是早早死了。它永远都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,不管我们是喜是忧,它都似笑非笑,—它到底“保”的什么“佑”啊?
爸爸妈妈虔诚地拜了一辈子菩萨,不但没有拜来兴旺平安,反而是麻烦一大堆!
这些年来,麻烦像树藤一样缠着我们家:兄弟姐妹几个,难得有几天天真烂漫、相安无事的日子。最小的姐姐说,她梦见有披头散发的女子来敲我们家的门;最小的弟弟被一些怪异的事情吓得不敢出门;我则在夏夜看见有黑影站在我们家门外……不仅如此,病痛的幽灵也特别“锺爱”我们家。二姐多病,哥哥在劳动时吐血……我也得了查不出原因的腹痛病,一痛十几年……
病急乱投医,人急乱拜佛。家中多年缠绕不去的难处,压抑着一家人。母亲分不清灾祸的前因后果,也是没有办法分清。她盲目地任着性子一路拜下去,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。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,我在母亲的啜泣声中醒来,目睹母亲正在烧香拜佛、念经哭诉……菩萨仍旧挂着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。母亲把一家人的命运都押在菩萨身上,那知这却是一个在空袋子里摸东西的举动,残忍得很啦!有谁来点破这个虚妄自欺的情形呢?
“凡制造偶像的,都必抱愧蒙羞,都要一同归于惭愧。”(以赛亚书45:16)其实,很早很早以前,圣经就警告人们,不要乱拜偶像;拜偶像的必然抱愧蒙羞。
父亲死后,家庭的重担都落在母亲肩上。看不到希望,原本寄托在菩萨身上的指望,渐渐断绝了。在无望和悲哀中,一天趁着哥哥姐姐不在,母亲就找了根绳子,准备了结自己的生命,追随父亲而去。母亲站在凳子上,手中的绳圈正挨近脖子,就在这时,我死命抱住了妈妈的腿;弟弟也拼命地哭喊……母亲回头看我们一眼,心软了,放下手中的绳子,搂着我和弟弟痛哭一场。
二、劳苦重担
母亲放下了死亡的绳索,却重新套上了生活的重轭。
二姐身体不好,病魔一直没有离开她。严重时,命悬一线,连医院都拒绝接收。一家人无能为力,只能听天由命。为了缓解母亲的压力,大姐撮合了一户人家,要将小弟送他们做养子。小弟走的那天,母亲哭得不行,弟弟也眼泪汪汪望着母亲,希望在最后关头出现转机……可是不行啊,穷人家庭,总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。弟弟还是被牵走了。
三姐芳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。后来,那家人有了自己亲生的女儿,于是三姐在养父养母心中的分量不住下降,受尽冷眼与苛待。三姐幼小的心灵,在缺乏爱、少有滋润的环境下,早早枯干和扭曲。及至成年,心如死灰,冷眼看世界。三姐独自漂流在异乡,她想家、想母亲,渴望有爱的生活。当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及的时候,生活有如味同嚼蜡。于是,三姐撇下两个孩子,在二十几岁时服下剧毒农药,离去了。
在伤痕累累中,使母亲的心稍得安慰的是二姐一家。二姐长大后,经人介绍嫁到了启东县。二姐身体有病,一直未得医治。不能下地干活,但二姐夫很爱她、关心她;丈夫的恩爱,使二姐苦难多病的生命得到了补偿。
爱,多么珍贵,是沙漠中的绿州。那长久不变的爱啊,哪里可寻呢?
后来,当哥哥娶了媳妇,我们有了嫂子之后;在贫穷和痛苦上面,我们家又有了争闹。贫穷和痛苦,让人绝望;争闹,令人怒气填胸。在绝望中怒气填胸,这样的日子很难挨。于是,我决定离家出走,自谋生路。
我先到了上海,做了一名建筑工人。每天扛水泥、抬沙筛沙,沉重的活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鼻孔老出血。老板不太在意工人的状况,只知催促人干活。到了年底,老板拖欠工资,钱没拿到。我短暂回到家中,很是狼狈。然而我们家,因为和哥嫂处不来,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块火石,一擦即燃,几乎天天着火。就这样,我再一次离家远走,到新疆碰碰运气。
1983年开春,我到了新疆,还是在建筑工地干体力活,抬石头。工头都一副德行,像赶牲口一样催着我们干活。有一天,做工时眼前突然发黑,昏倒在地上。工头把我带回宿舍,放倒在床板上,丢下两块钱让我到连队医院看病。因为身体发虚,走在去医院的路上,我再次昏倒,是连队士兵将我送到医院的。回来的路上,一位陌生的阿姨看我走路吃力,摇摇晃晃的,就扶我到她家中,为我端上一碗鸡蛋面条;在异地他乡,我一边吃面条,一边掉眼泪。
中秋节到了,工地上发了月饼。望着天上的月亮,我却吃不下手中的月饼。我的心跑回到母亲身边,牵挂着母亲的近况。我不知道母亲在这个中秋能不能吃上月饼。拿着月饼,却没有心情送进嘴里,我不愿一个人独享口福。我将月饼送给工地上年长的陈师傅,说:“陈师傅,请你吃这个月饼,代替我的母亲吃。”那知粗人惯了的陈师傅,却不体会我的心思,随手将我含义深刻的月饼满不在乎地丢给了丁师傅,说:“你吃。”丁师傅是个时常贬我的人,这事对我的打击蛮大。
新疆之行,好运没碰到,失望反倒增加一大把。我手拿一张火车票和三十块钱,再次溜回家中。家里的情况仍像一潭死水,看不到希望,也不能改善人的心。母亲仍是执迷不悟,在越拜越糟,越糟越拜的框框里打转,出不来。一个大活人跪在一个像人一样的木头面前,求这求那,想起来也真是可怜。那些时间,我小时候就有的腹痛病时常发作,父亲生前做巫术的朋友提议我吃香灰、喝仙水、拜庙求医治。但毫无用处,病情非但不见好转,反倒有加重的苗头。医院还是查不出因由。
“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,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……”(诗篇31:10)
我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,在江阴打石场干过一阵子之后;二姐看不下去了,劝我学一点手上活路,这样更适合我的体质。我觉得这也在理。于是,物色了一个裁缝师傅,做起了裁剪工。师傅待我不错,我很快学得技术,并且可以出师自立门户了。虽然已经薄技在身,然而我所盼望的转机并没有临到我。
三、浪迹在外
1989年秋,我身带几元钱的盘缠,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,再次走出家门,浪迹四方。虽然没有想好要走的方向,但迷茫中,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向西,走了一百多里路,心里还在自问,我到底要上哪儿去。跑了几天,又饥又乏,身上的盘缠早已没了影儿。于是,走什么田地唱什么歌,我甚至硬着头皮向别人要东西吃。那情形,跟圣经中浪子吃猪食的狼狈劲有得一比。浪子吃尽苦头后,心眼通了,就满心后悔,终于回到“口粮有余”的父亲家里。但那时的我,仍苦苦挣扎于人世苦海,我的归途在哪里?我可以平静躺卧的港湾在哪里?不得而知,也没有细细想过。
到了南京,有一个同乡看我风尘仆仆,就有心留我住几日。但同乡的日子也不宽裕,增加一份年轻人的口粮,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于是我就没好意思留下来。离开同乡处,我打算到安微九华山做几天和尚,清闲清闲。但人算不如天算,听说那边的和尚职分要有文凭,我没有大学文凭,只好作罢。现在想来,我没有迈入寺庙的门槛,是天意、是神的拦阻。因为圣经上说过:“人的脚步,为耶和华所定;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?”(箴言20:24)
世界很大,大到一望无际;世界很小,小到没有立锥之地。几经折腾,还是没有找到南京立足的地方。方便的是,我没有多少碍手碍脚的东西,可以来去如风。既然已经浪迹江湖了,那就应该继续“漂下去”。至于什么地方,那就没有多少讲究了,横竖都一样。我花8块钱买了一张到荡山的火车票,上车后我便呼呼睡去,直到广播里通知检票,我才醒觉过来。于是赶忙就近下车,下车后方知这是到了河南的义马市。
天空正飘着雪花,地上已铺了一层老厚老厚的雪。我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,缩着身子走在铁路上,那味儿,不光身体在流浪,心灵更是在流浪。流浪的身体需要食物来满足,心呢?流浪的心如何得满足?
走着走着,终于停下来了。一个老汉主动上来与我搭讪,问我是否需要找一份活儿干干。估计我那时的模样,就跟挂着副牌子一般无二,上面写着“我要干活”的字句。
老汉的话,就像问口渴的人是否需要水喝一样,正合我意。我自然马上点头答应。以后为了拉近和老人的关系,我还认老人为干爹。以临时确定的“亲情”,来稳定我们的关系。可见人是多么需要友爱,甚至不妨以模仿血亲的方式来获得。这样,我就在义马煤矿做了一名装卸工。
到了秋季,我碰巧看到一张广告,是张招聘广告。这些时间,我的情绪变得很糟糕,心里总有一点气愤愤、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味道。换工作,就像是换鞋一样,再也平常不过。看完广告,我就去鞭炮厂应聘,做一名装火药的工人。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,一旦出事,有生命危险。但报酬比较高。我是带着一副死了拉倒的态度去上岗的。十一月二十五号那天,鞭炮厂果然出事了,装药车间发生爆炸,成品都炸掉了,有人被炸伤。我却逃过一劫,因为那天刚好我在外面办事。但有一个念头却是时不时跑出来发问,为什么我不在事故中被炸死呢?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?
因为这次事故,鞭炮厂垮掉了。我又变得无事可做,只好回到干爹那里,再作打算。干爹见我现在的处境,就像一根腊肉骨头,用处不大,但又舍不得完全丢掉。一天,他沉着脸说,耗着也是耗着,不如像他们一样,爬到火车上去扔点东西下来还好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在火车上做个偷儿,也叫“车匪路霸”的那号人。干爹并且事先申明,万一出事,可不能供出他来,要不然就要给我好看。
又是一个下雪天,我空着肚子爬上鞭炮厂附近的山头,又冷又饿。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,少有来人。冷风在坟堆的树木间回荡,呼叫着吹过身上。我抓起两把雪,想塞进嘴里,因为实在饿得不行了。“小赵,小赵。”就在这个时候,听见有叫我的声音。奇怪了,这个平素也难得见人的地方,竟有人叫我?更何况是风雪交加的时候。但这是真的。来人已经站在面前,拿掉我手中的雪,塞入两个馒头。他们是专门来看我的。他们说他们是信耶稣的,听说我的情况后特意来看我。那些人为我难过,请我住进他们家去。但我谢绝了。我不想再给这些人添麻烦。但耶稣这个名字,留在了我的心中。
生活的苦头吃得多了,就像零件少了润滑油,心思开始叽嘎叽嘎出毛病了。人变得怨天尤人,总觉得别人待自己不公,而自己老在吃亏……没有正确的态度面对这些人生难题。久而久之,人越来越苦毒,也越来越悲观厌世。
我曾两次尝试自杀,第一次是吃安眠药,没有死成,反而落得被人笑话。第二次,记得那是一个日落黄昏的时候。我跑到一个离涵洞不远的地方,卧在铁轨上,准备以这种方式寻短见,然而也以失败告终。当我横卧在铁轨上时,由于疲劳,很快睡着了……正当我在梦中大吃大喝时,火车的鸣笛声将我惊醒。懵懂中,一瞬间我甚至搞不清我是继续活着还是已经死掉。过一小会,有人跑来向我发问:“你怎么样?”我才确定自己仍然是一个活人。跟我说话的那人可能是一个乘客,他接着说:“没受伤赶紧跑吧,要不然会挨揍!”于是我就跳起来,向山上一溜烟跑去,消失得很快。连后面骂我的声音都没有听见多少。这一次,因为火车即时刹车,我又捡回一条小命。
“我们不至消灭,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;是因他的怜悯,不至断绝。”(杰里迈亚哀歌3:22)
四、出死入生
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,我又过了几年。直到1993年秋季,我的生命才发生转变,因为这一年,我认识了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一年,我在孟津的一家乡村服装厂干活。这家服装厂的效益不好,时常发不出工资。工人们脸上都罩着一层愁云,因为一个月的辛苦,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有一天,坐在办公桌前,我的心思活动起来,想起几年前在雪地里的那一幕,心中有一股暖流升腾起来,这是很少有的愉快经历。于是,我随手在一张纸上画下一个十字架。心想,信耶稣的,就是不太一样啊。
恰在这时,一位女工走进办公室,平素我从没见过她来我们办公室。她进来一眼看见我画的十字架,就高兴地说:“你也信耶稣?”我说:“没有。听说过。”她说:“耶稣爱你!”我笑笑,算是待人以礼。她进一步说:“我看得出,你心有忧愁。信耶稣吧!耶稣能拿去你心中的愁苦。”女工向我发出邀请,要带我去她们教会看看,我则怀着看看也好的心情答应了。
到了教会,我看见许多人正闭着眼睛祷告。女工对我说,你也可以祷告,求神拿去你心中的愁苦,赐给你平安喜乐。然而,我的心思却漫游起来,想起家里常有的情形,就是父母在菩萨面前的模样—念念有词,无比虔诚的模样。我的心打鼓了,这不是花样翻新的迷信活动吗?这跟拜菩萨有什么两样?女工真诚地对我说:“耶和华神是真神。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。人类犯罪堕落以后,就没有法子再见神的面了。不光如此,人犯罪以后,咒诅就临到身上,死就成为一个人人躲不过去的坎儿。人人都有一死,死后且有审判。要想免除灵魂下地狱的厄运,只有来信靠耶稣基督;他是上帝的独生子,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……”
我也是一个罪人?原来我以为只有那些折磨苛待我的人才是罪人。但听女工一席话,我才知道,是不是罪人要从人的心里活动来衡量,心里有卑污可怕的念头,人就从里面坏掉了,就是一个罪人了。如果这样说,我也是一个罪人啦。我在红着脸面和哥嫂吵架的时候,我恨他们;我曾因一个漂亮女人引诱我,我拒绝按她的意思行苟且事后遭到报复,被赶出收留我的张伯家。为这事,我曾恨上所有的漂亮女人,巴不得用刀杀尽所有漂亮女人,这些都应该算为罪呀!心里这样想,但对罪的理解还是挺模糊的,甚至有点不情愿。
那天传道人讲道,有句话如当头棒喝,给我沉重一击:“耶和华如此说:‘倚靠人血肉的膀臂,心中离弃耶和华的,那人有祸了!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,不见福乐来到,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,无人居住的碱地。’”(杰里迈亚书17:5-6)这句话不就是对我说的吗?我一直以来的人生路程,不是倚靠自己、就是别人血肉的膀臂,结果真的是有如住在“旷野干旱之处,无人居住的碱地”啊!生活、心灵都枯干到了极点。
一向对听歌打不起精神的我,在教会的赞美诗中,却感觉到一种甜美和温暖。那曲调,令人想起父亲慈祥的目光,母亲温柔的臂弯。赞美诗唤起我许多的回忆和向往。尤其像我这样一个人生多险途的人,赞美诗真像一剂润滑剂,滋润着我。我在人生的极难处,经历过好心人“雪中送炭”的救助。但老实说,这是极稀罕,也是缺乏持久和稳定性的,随时会因着种种的变故而烟消云散。莫非赞美诗中的耶稣基督,才是我遍寻不得的绿洲,爱的绿洲,并且长久不变?后来,在聚会中,我自持不住,就哭起来,哭得很伤心。像圣经中的浪子终于回到父亲的家,“主耶稣啊,求你救救我……”
信主后,心里好像有了一位密友,可以随时与他交谈、求问,请他帮助。一天,我正有气无力走在乡村的土路上,三天没有卖掉一件衣服,吃饭都快成问题了。再没有点进账,下午连碗面条都吃不起了,心里七上八下。就在这个时候,一条狼狗也好像看出我的软弱,狂叫着冲过来要欺负我。我边跑边向耶稣求救,心中害怕得不行。但稀奇的事发生了,待我跑出几十米,我感觉狼狗并没有直追过来,连叫声都停下了。我好奇地回过头去看个究竟,狼狗正愣愣地站在路中间,它脑袋的上方有两只鸣叫着的乌鸦在盘旋,把狼狗吓住了,呆立在那里。
耶稣基督以奇妙的方式及时帮助了我,带着一股兴奋劲,我继续向他恳求:“耶稣啊,你知道,衣服卖不掉,我的肚子饿了……”耶稣真好,过了一会儿,他就感动一个女孩子来买我的衣服,解我燃眉之急。女孩子看中一件衣服,我知道乡下的孩子不富裕,就平价以10元钱卖给她。这下可好,10元钱,我可以高兴咋吃就咋吃了。
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,是我们的力量,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”(诗篇46:1)这句话,就以这种方式进入我的心灵。
1994年春节,是个不一样的春节。这一年的春节,我是在教会过的。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肢体间无私的关爱。我是一个长期离家在外的人,每逢节日,我们中国人的亲情观念都会集中爆发一下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诗句,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。往年,每当节日临近,心里反倒倍感孤单落寞,别人的喜庆欢快,却是我的凄风苦雨。这一年春节,弟兄姐妹知道我是外地人,又是个在主里初生的婴儿,他们把爱心加倍地放在我身上,使我这个属灵“婴孩”仿佛是在爱的溪流里,如鱼得水,很是欢快。“神就是爱,住在爱里面的,就是住在神里面,神也住在他里面。”(约翰一书4:16)
然而,撒但最不乐意看到人被救出他的黑暗王国,进入光明国度,成为光明之子。他会使尽手腕干扰破坏,试图把人重新拉回他黑暗的圈中去。有一次,当地的妇女主任托人找到我,说为我找到一户人家,家庭条件很好,那家主人愿意认我作干儿子,这样就可以有个好靠山。妇女主任还说:“就不要信耶稣了,还是靠人帮助来得实在。”我对妇女主任的回答是:“阿姨,什么都好说,但让我不信耶稣,我做不到。”
五、奉献自己
信主一段时间后,我仍然希望在生意场上发展。对于神在我身上的旨意,我寻求得不够,始终是按自己的意思在安排生活。后来我干脆转移到洛阳做服装生意。生意做得仍然跌跌撞撞,并不顺利,甚至还落下几千元的欠款。我再次陷入苦闷中,也只有在苦闷中,寻求神的心意反而更为强烈些。有一次,我到附近一家教会参加敬拜,得知教会近期有神学培训,我很渴望参加。弟兄姐妹见我有热心,就帮助我实现心中的愿望。
一直以来,在罪的问题上,我都存在理解问题。有一天,神借着传道人的话,光照我,使我茅塞顿开,清清楚楚意识到: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大罪人,只配下地狱的大罪人。祷告中好像一道闸门打开,过往生命中罪的污泥浊水滚滚涌出,我整个的人就是一个罪的大水池:我曾经怂恿母亲摔碎表姐的茶瓶……亲手打表姐喂的羊,打得羊鼻流血……拜偶像、吃香灰、算命……我真是里里外外透着罪,罪的花色、罪的质地,这就是原来的我。感谢主,像我这样一个只配丢在硫磺火湖里的人,主还用宝血洗净我,拯救我,称我为义……主啊,你的恩典我没有办法报答。如果主使用我这颗原被废弃的螺丝钉,这就是我莫大的福分了!
那天,当传道人呼召时,我心甘情愿走出来,愿意奉献自己为主使用。传道人来到我身边,郑重地说:“你还与什么人有嫌隙,没有解决吗?”我一时语塞,没有立即作答。传道人继续说:“你和你哥哥,现在怎么样了?”我很诧异,不知传道人如何得知我和哥哥的关系一向不和。他劝勉道:“你要和哥哥和解啊!”就像雅各布和他哥哥以扫和解一样。
以后,我被慧姐妹用三轮车接到她家中暂时安顿,慧姐妹父母待我很友善。这段时间,我在团契中读经、祷告、灵修,生命得着长进。身心灵都有安息,也得着神的医治,多年困扰我的胃病已得痊愈。有天上午,我和慧姐妹正在商量诗歌班的事情,刘姥姥进来,干脆地说:“你们两人的事,我祷告了,你们结为夫妻吧。”慧姐妹的爸爸也同意我们的婚事,慧姐妹自己也说,她在祷告中的领受,是她要嫁给一个外省人。感谢赞美主!像我这么一个流浪儿,原本想都不敢想的事,主也替我成全了。
1995年3月的一天,我和慧姐妹跪在上帝面前,在隆重的赞美诗中接受从上面来的祝福,我们结婚了。在上帝面前,我们立下誓言,永不变心,忠心服事主!
以后,我和妻子回到家乡,向我的亲友同乡传福音。我的母亲也离弃偶像,归向真神。最感恩的,是我和哥哥已完全和好。哥哥信主后,我们还常常躺卧在一起,分享心中的喜乐、见证主的大爱。感谢主!